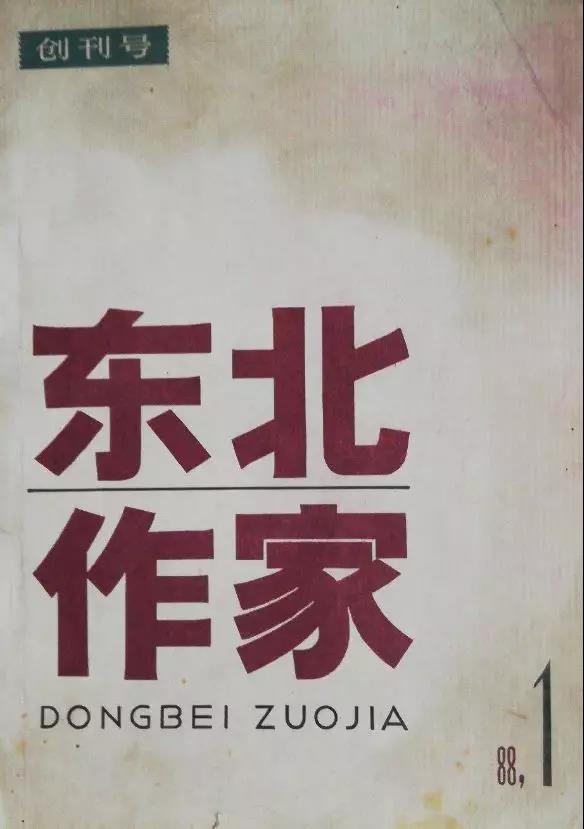罗振亚:李琦长诗《死羽》, 朝圣路上的精神漫游? | 名作欣赏
来源:2011年第2期 作者:罗振亚 时间:2019-11-18
朝圣路上的精神漫游
——李琦的长诗《死羽》重读
文/罗振亚
李琦的长诗《死羽》发表于1988年《东北作家》创刊号,随着时间的推衍,它的影响越来越大。抒情主体李琦的现实信息源在俗称“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抒情客体《死羽》的文本信息源却发自西北高原。西北与哈尔滨,两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是怎样奇妙地邂逅并复合在同一精神空间的?这是我面对《死羽》时最初的疑惑与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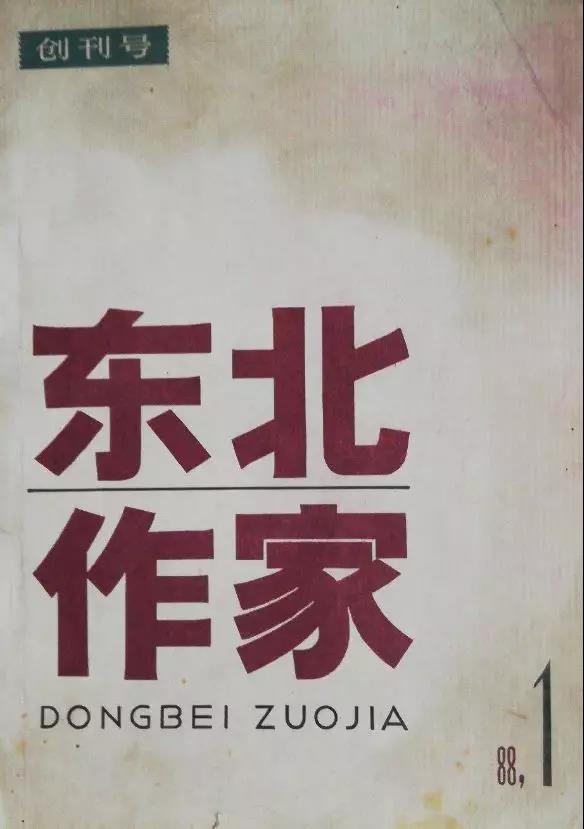
洞悉诗人的心灵后也许不难寻找到答案。李琦不乏浪漫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强劲的内趋力,为她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并保证了诗歌审美价值的生成。而这种精神气质中的乌托邦假设与残酷世俗现实冲突的无法调和,势必导致她不时产生一种天然而强烈的人生需要,一种“精神”逃亡的冲动,不满于庸常存在境况的单调与贫乏。她痛感到都市物欲膨胀、精神孱弱的人类异化,那里只有生活而无生命,理想的真正的“生活在别处”,进而渴望寻求一种神秘未知的事物,一个梦魂萦绕的精神“远方”,以达到内在心灵的丰富与生命活力的恢复。那么为什么诗人向往的“远方”不是文化悠久、喧腾繁华的中原,也不是花团锦簇、四季如春的西南或东南沿海,而偏偏选择了相对偏塞荒寂的西北?我想这绝非仅仅因为画家朋友讲述的“三个小麻雀”故事的吸引与诱惑,恐怕与蛰伏于诗人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不无关联。不错,西北乃荒凉神秘的所在,可是它自古以来就好像与缪斯女神有着一种天然的默契,是诗的别名,从千余年前王昌龄、岑参等领衔的边塞诗,到杨枚、周涛、章德益、昌耀为主体的当代西部诗,不时有一股粗犷而悲凉的声音穿透岁月的屏障遒劲地传出,或者说西北的广袤与开阔、博大与平静宜于放牧自由的诗鹰。另外,我也曾不无怪诞地联想到西方是太阳与光明的故乡,西方是朝圣的方向,当年陈玄奘取经的目的地是西方,李琦的“径直往西去”是否也暗合着这一思想脉动?因为1986年诗人应和远方呼唤的西北之行,就是一次心灵的朝圣,《死羽》就是朝圣路上的精神漫游啊!
象征架构与形上旨归
创作《死羽》时李琦正值而立之年,但不同凡俗的直觉力与亲历西北的体验,却把她引入了幽深的思想福地。
五百行的抒情长诗《死羽》由十一节连缀而成,其涵容的时空舒展而宏阔。时段是:十五年前——1986年——几个世纪之后;空域是:哈尔滨——北京——乌鲁木齐的车上——酒泉——小镇饭馆儿——沙漠——安西——玉门——阳关——敦煌。浩浩数百年,茫茫半个华夏,特定的时空坐标中跃动着诗人西北行程的所视所闻所思所想的细节或片断。少女时代诗人的心扉因读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而洞开,渴望“当一个诗人”;十五年后,女友讲述的“三只小麻雀”的故事,唤回诗人十五岁时的激动,她决定“去西方”;旅途中,哈萨克人阿斯哈尔、残疾的转业军人、北京籍老阿姨的人生经历织就的“温暖的情节”,伴列车前行;烽燧、高原、戈壁、羌笛、白骨、泪腺,“一路向西的风景”,使旅途的浪漫心事渐趋沉重雄浑;酒泉的苦爷有着苦难的命运,但仍仗义而顽韧地“向往飞”,他的遭遇与性格深深打动了诗人;清真饭馆,诗人因牵挂陌生的流浪人,一改平素烟酒不沾的习性;走入九月的沙漠,诗人忽然生出前生曾飞抵过这里的幻象;在安西、玉门、阳关,小饭店营业员称呼的亲昵从容,小伙子从山坡上摘花馈赠的真诚,维族阿妈特意烙制带有美丽图案贺饼的善良和体贴,令诗人双眼酸涩,感动不已;从敦煌飞天女神的形象里,诗人领悟出生命与生命的意义,于是在心中生命的消遁与诞生同时完成;诗人没能找到那三只麻雀,却时时感到它们辐射的气蕴,所以“归来的路上”,不住地噙泪回望圣母般的雪山;最后诗人幻想几个世纪后,自己化为晴空下朴素的小麻雀,羽翅“飞成美丽的弧形”……诗的底层视象呈现的就是这些,就是西部自然、风情与诗人思绪的分散又连贯的片断流转。
但是如果我们的解读停留于此,就无疑是糟踏了这首诗,等于说它仅仅是诗人思想经历的客观恢复与无为观照。事实上该诗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诗人所写的一切既是实指又别有用意,它摆脱了一般游记诗对一草一木、一情一境精巧描摹与动情歌吟的感物抒情的窠臼;而是以一种从心理体验出发的、探寻灵魂沉沦与飞升的深刻哲思贯通全诗,巧设饱含暗喻、象征的符号系统框架,高屋建瓴,从而激发出诗情绪与理性混凝的多层面复合型题旨,昭示出大诗人必须追寻的路向。
在诗的象征性框架中,“小麻雀”与“我”是两个交互出现、渗透的主体层面。在十一节诗中,小麻雀一直隐现于诗人心中并规定着诗的运思方向,仅显性出现就达十三次之多。若按照新批评的理论阐释,“三只小麻雀/三颗勇敢的心”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天赐的隐喻”、“物化的象征”,而小麻雀这一主体中心意象对文本的介入与贯穿,自然也就赋予了诗歌一种言外之旨,使外在视象背后有一种形而上的深层意味与旨归。小麻雀究竟象征着什么?文本的整体蕴含又是什么?我以为麻雀意象在诗人主体融入后已从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交锋中出离,由自然界纯粹的静物转换为诗人智慧与生命力放射的载体,它是对活力求索的翘望,不屈精神的聚焦,并对深陷精神困境的诗人提供了天启神示。在“只有梭梭草和热风”的死寂戈壁,在大山荒漠、黄沙雪土的险恶残酷空间,在布满兽骨、泪腺、烽隧的死亡地带,几只小麻雀无畏地飞翔过、追寻过、歌唱过,即便生命陨落了,它们并排躺着的躯体,仍然将“三只小头颅/向着苍茫的远方”,生死不渝地坚守追求的方向、希望所诱惑的方向。悲凉而荒僻的画面里,那种奔突着的生命力激情令人佩服,从那飞动的生命活力中,感动的诗人顿悟到“原来世界在有道路之前/是先有了无畏者的梦”,并达成了灵魂与小麻雀的融浑。
多么朴素又警策的隐秘灵魂音响啊!不是吗?梦和理想缤纷绚烂,美妙诱人,人类历史正是凭借一个个梦与理想的贯连支撑才蜿蜒前行的;但梦和理想的道路并不是顺畅的坦途,它的实现也需要付出代价,真正勇者的使命就是去开拓,风沙荆棘遮蔽不了他眺望的视线,死亡与恐怖阻止不了他跋涉的步伐,为了远方一切都在所不辞,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如若这样度过是值得的,它的肉体可以静止乃至消失,而精神却将走向永恒与新生。正是这“勇敢的心”,给诗人以及那些失望者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夯实了他们无愧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信念;正是这穿越精神荒漠的力量启示,激起了诗人生命与思想的激情,敦促她在拒绝被外部环境物化的同时同内心自我的淡漠搏斗,顽韧地进行人生苦旅的追寻。原来诗人不懈地寻找那三只小麻雀,就是在寻找一种理想、一种希望、一种已钝化的生命活力!那种追天问地的求索精神,与《离骚》中屈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如此说来,西行之旅不是心灵的朝圣又是什么?
在西北生命活力跃动的空间形式中,沐浴李琦灵魂的不止求索精神的启悟,还有美善一统的人性良知的光辉。诚如一位论者所言:一趟西北之行拨亮了她心中的灯盏,于是她借那古朴的民风张扬了共在中应有的伟大的人类精神。李琦西北之行足迹所至的确是荒蛮偏僻的世界一角所在,那里没有摩天大楼耸立、霓虹灯闪烁,那里缺少迪斯科节奏、先进的科技媒体,仿佛与现代文明处于被隔绝的状态。但世上许多事物都是祸福相依,现代文明推进了人类历史,同时也付出了遗失许多宝贵东西的代价,如人类情感的纯真、关系的亲和与生命的强力。西北的落后令人遗憾,但也因为其落后闭塞反倒未被现代文明完全浸染渗透,存留下一些原始纯朴的民风、自在的生命形式与未被人工化的自然景观等等。恰恰是在这片现代文明之风不很强劲的土地上,诗人发现、捕捉到了人性乃至神性的辉光,并寄寓了自己的情思的理想旨归。
具体地说,在西北风情风俗风物聚合的画境中,诗人透析了西北绵绵悠长的生命情调,触摸到了西北人热情善良、坦诚粗犷的灵魂内核。那些并非中心的穿场式人物,也都可以视为象征人类神圣良知的语符。卖瓜的苦爷,在一个寡妇危难之际仗义地伸出援助之手,以勤劳与微笑扛起沉重的义务,当那女人被迫离开他时,他坚忍地接受了,把自己变成戈壁上的“第一片戈壁”,以后的几十年每月都汇款给那位寡妇,他这“没有家受了伤的鸟”“还向往飞”,那份坚忍达观沉默豪爽让人敬佩又心酸。还有那位采油钻井队的小伙子,青春放牧在荒凉的地方,满肚子苦水,非但不抱怨,反而仍能对陌生人以诚相待,将一束并不美的“干不死”花送给诗人,献上一份衷心的温情祝愿。还有那位外国美丽的姑娘柯瑞嘉,她与诗人一见面就卸去了心的伪装,一见如故,一同吃拉条子面,讨论诗人自杀问题……无论是西北的土著居民,还是寄居西北的创业者,抑或是来西北的旅人,活动于抒情空间的具体的几个人(“我”、丈夫、阿斯哈尔、转业军人、北京籍老阿姨、苦爷、流浪者、柯瑞嘉、营业员、小伙子、阎红),无不本色纯真,散发着神圣的气息。正是受其感召,原本有温婉慈爱善良的母性情怀的诗人,对遭逢的每个生命都奉上一份理解、关爱与祝福,对营业员、小伙子、维族阿妈充满谢意,对陌生流浪者充满惦念与牵挂,并在关爱他人过程中得到了人生价值实现的快乐。正因有了西北的点悟与参照,愈发觉得都市乃是人性扭曲的昏天暗地的诗人,面对西北这一片戈壁、雪山、敦煌石窟组构的“亲山爱水”,沐浴着这—片人与人理解沟通友善的人性的阳光,抖落了城市附加给人的精神尘埃,禁不住为找到生命与理想的故乡而感恩不已,感动不已。
在她看来,西北存在的才是真实而美好的人性世界,西北人的生活才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与栖居!她对西北人生状态的宣显,可以说是对人类本真与良知的深情呼唤,是对人类被异化的生命的苦心招魂。它无疑体现了诗人理想主义的文化心态和对生存意义、生存价值的终极关怀。
长诗在结构上以寻找麻雀起领,以未寻找到麻雀结止,寻找的思想红线贯穿着首尾两极,诗人有意营造的这种封闭结构与象征性框架的遇合,使诗在底层视象上的高层空间弥漫着浓郁的哲学思辨氛围,有了一种禅宗意味。禅本是静虚止观之意,禅宗的中道义是一个虚无的不可把握的东西,属“无”的范畴,它的最高乃是“空”,让人追求心无挂碍的灵魂会悟。的确,诗人没有找到画家朋友所说的小麻雀的尸体,但小麻雀的飞翔精神与身影不一直伴随诗人左右吗?在西行列车上她“总是看见/三只小麻雀/在比肩飞行”,就是在未找到麻雀的失落中,她的视境中“却总有三个小小的身影/却总有漫天飘飞的羽毛”。这正应了禅宗在不可思议处思议的思维方式,揭示世上那些看似假的东西往往都是真的,因为在禅宗看来虚即是实,无即是有,没有找到自然即是找到了。原来小麻雀就生长在诗人的心中,就生长在诗人的感觉悟性里,并且,从象征意义的层面说它们就生长在西北人的灵魂深处。维族阿妈贺饼图案中“是一只飞翔的鸟儿”,那位苦爷,那位残疾的转业军人,那位有结卤意志的流浪者,那些有家没家的、受伤未受伤的人们,不都是一只只“向往飞”的麻雀吗?尤其是诗人与麻雀意象的互渗,已使二者泾渭难辨、主客融汇,她对希望活力矢志不渝的求索的那份执著、那份专一亦不正是一只只给人以生命启迪的小麻雀意象的外化与代指吗?
优秀诗歌的文本内涵是无法穷尽的,具有不可完全解读性。《死羽》的意味旨归是个多维系统,也许诗人还有更深的蕴含企图,也许读者将会有更新的思想发现。读《死羽》我总挥赶不去艾略特的《荒原》、屈原的《离骚》的影像,我不知道《死羽》与后二者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但流贯诗中的内在精神却如出一辙。只是从《荒原》中读到了绝望,从《离骚》中读出了忧伤,从《死羽》读出的是一种向上的力量。

平衡:寻求突破长诗艺术的探险
文章大体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作品面世不久即成隔日黄花,难再为人提及;第二重文本活上十年尚有人咀嚼,这对作者已属莫大的福分;第三重是文本生命长于作者生命,人虽仙逝数载,作品仍被不停流传。从这个意义上说,《死羽》至少已跨入文章的第二重境界,二十二载时间河水的冲刷,它还光彩依然。
1986年对于李琦是值得庆幸的。这一年《死羽》的写出为其灵魂与想象力的飞腾寻找到了载体,标志其诗艺攀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同时为汉语诗界长诗艺术的突破传送出可借鉴的信息。必须承认:作为泱泱诗国,中国的短诗已臻出神入化之境,但史诗与抒情长诗的传统却相当稀薄。原因是复杂的,因为史诗与抒情诗既需历史提供机遇,又要诗人具备兼容大度的艺术修养;东方式的沉静与个人经验、承受力、客观理性的牵制,也不允许中国诗人过分涉及艾略特的《荒原》一样的领域。到了新时期这一缺憾更为显在,抒情长诗一再被忽视,中间虽有江河、杨炼、廖亦武等人倡言寻根史诗的试验,可因当代意识的烛照不足,到头来只是让读者嚼了一通传统文化的中药丸。而任何一个诗人或诗歌运动成熟的标志,就是抒情长诗、史诗等鸿篇巨制的诞生,否则就难以企及辉煌。李琦的可贵之处是作为诗感与思想素质俱佳、学养丰厚的诗人,她对宇宙、人生、社会都有独具慧眼的发现认知;但又能不为知识所累,而仅仅以其作为背景存在,不靠移植西方的哲学思想哗众取宠,也不做玩弄技巧与意象拼贴花样的形式主义者,她是通过对自己良知与灵魂的引爆,用生命与直觉写诗,探寻人类生命价值等超越性的精神命题,所以开辟了一方簇新陌生又深邃异常的审美经验境界。不知她是否有意为之,《死羽》把相对或异质因素掺合一处,以一种平衡综合的艺术风度来激发艺术张力与多重复调感,这种大诗人才具有的姿态与探索,尚不能说完全成功;但至少为汉语抒情长诗的写作输送了新的质素。
《死羽》艺术的首要特征是主客互动,综合了抒情与叙述二维因素。西方传统史诗强调客体之实,叙述主体与叙述客体的距离感处理不当会陷入沉闷板滞的泥淖;东方的抒情短诗传统则崇尚主体之真,张扬情感的自然诚挚与强烈,弄不好会走向凌空蹈虚的偏狭。深知此中三昧的李琦没有偏向其中任何一维,而是逸出传统之圈,谋求两维融汇,主客互动,叙述与抒情的交相穿插,创造新语境。
为避开长诗易迷失的向议论、理性概括倾斜的误区,不使自我扩张淹没诗艺的魅力,诗人吸收了史诗规范意识的合理内核,重客观“叙述”的表达方式,再现西行经过、经历的人与事,甚或有点儿小说化、戏剧化企图。于是数位个性鲜明的人物与情节片断走进了抒情空间,如:
并不完整的故事碎片,已使苦爷的精壮强健、仗义善良从形到质地耸立起来。
无须多言,只是一段简洁的叙说,一截假腿镜头的摄取,已使转业军人对西北饱含悲怆的生死之恋力透纸背。于是大量戏剧性细节与景物画面蜂拥而至:
蒙太奇式意象的跳接,自古而今、由东至西的一段历史、自然风光尽收眼底。因为客观性叙述因素压着阵脚,《死羽》中不但时间与空间视域十分宏阔,带着史诗的一定的文本特质,而且也避免了情感的夸饰与想象的虚浮。
如若通篇都是客观叙述状态就难免沉闷板滞,因此诗人又融入了大量的抒情因素。它让主体“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接介入,从幕后走到台前,于是一曲曲西行的心灵颤音弹拨而出;主体的心灵抚摸使诗中的人、事、物等叙述因素都不同程度地浸染上了主观化色彩。在交待十五岁读普希金诗的感受时,诗人写道:
毫无设防的心绪淌动,烘托出一个充满幻想的浪漫诗人的存在,正是这种气质促成了诗人三十岁时西北的诗性游历。西行途中,诗人面对神奇的敦煌艺术,面对肌肤丰腆、反弹琵琶、云鬓高耸、裙裾飘飘的飞天女神,忽然悟到自己的美丽与幸福,禁不住喃喃说出“一种美丽的感动如雾/弥漫了我整个灵魂/我忽然明白了/生命”,人比神更动人,艺术书写的是人的永恒。众多心曲穿插在故事的交响中,灵动活泛,拉近了诗歌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阅读时顿感一阵亲切之风拂面,迅速沉入诗人设置的浓郁情境之中。可见,叙述与抒情并非常人视若水火不容的两极,它们在《死羽》中相生相克,相得益彰,强化了诗的具体可读性的肌质与真切可信的亲切风格,共同保证了诗美之鹰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