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前语:惊闻我刊老作者、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离世,编辑部全体同仁深感悲痛,兹谨致深切哀悼。
从1985年开始,富仁先生先后在我刊发表30余篇文章,这些文章是先生研究生崖中的重要成果,承蒙先生信赖,得以第一时间通过我刊与读者见面。前年,先生还把他的文章《中国需要鲁迅》交给我们,发表在2015年第6期本期头条栏目。今天,先生离我们而去,我们把这篇文章通过微信再次刊发出来,与各位热爱鲁迅先生和富仁先生的读者共享,同时表达我们对“大先生们”的怀念。
富仁先生千古!
——《名作欣赏》编辑部
中国需要鲁迅
来源:《名作欣赏》2015年6期

我们在“文革”前就搞鲁迅研究的学者,总觉得现在社会上反对鲁迅的人增多了,感到有些受不了了。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自从鲁迅逝世之后,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鲁迅精神和鲁迅作品获得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最多也最深刻的时期,并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着。远了我不敢说,但我可以断言,在今后的二十年内,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鲁迅将赢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价值和意义将表现得更加鲜明和充分。
“文革”前的鲁迅研究看起来很红火、很纯粹,人人把鲁迅捧得很高,但那时的中国真的像表面看起来那样重视鲁迅和鲁迅精神吗?实际上,在那时,鲁迅与中国的国民乃至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读鲁迅不如不读鲁迅。连我们这些当时的小青年都知道,研究鲁迅的容易成“右派”。那时的人只能住在一座思想的房子里,但这座房子不是鲁迅的房子。新时期以来,思想开放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下子散开了,但他们不是从鲁迅的房子里跑出来的,而是从另一座思想的房子里跑出来的。这种一哄而散的现象未必是一桩多么好的事情,但中国知识分子跑散了却是事实,他们大多数没有跑到鲁迅这里来也是事实,但到底有一些人跑到了鲁迅这里来。只有到了这时,这些人才真心地感受鲁迅、思考鲁迅、阐释鲁迅,而不是用鲁迅阐释别人的思想。在这时,确确实实有好多知识分子离开了鲁迅,他们过去是说鲁迅好话的,现在不说鲁迅的好话了。凡是这样的人都是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鲁迅的。我们现在好说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最难变的就是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一个人可以从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处来变到看出它的好处来,却绝对不会从看出一部作品的好处来变到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处来。一个人一旦喜欢上了一部文学作品,一旦建立了一种思想观念,往往终其一生都是不会变化的。变了,说明他原来就没有,说有那是骗人的,是跟着别人乱起哄。只要看一看我们现在的那些鲁迅研究著作,特别是现在的中青年鲁迅研究者的研究著作,我们就会感到,现在真正感受到鲁迅伟大之处的人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鲁迅与这些作者在精神上的融合程度甚至超过了与胡风、冯雪峰、李何林、陈涌那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立起对鲁迅的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正在重新发芽、重新滋长,并且不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变化,这些人的鲁迅观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了。我很看好现在的鲁迅研究。我们已经不能依靠一部鲁迅研究著作升官,也不能依靠一部鲁迅研究著作发财,但还是有这么多人研究鲁迅。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呢?
对鲁迅的不满是有的,概括说来,这种不满来自以下四个方面,但我认为,这四个方面的不满都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它们都不是绝对地远离了鲁迅,而是在一种文化趋向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社会的思想总是在流变的过程中,一个人的一生也有从幼年到童年、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的诸种变化,即使在同一人生阶段,人的思想感受也不是绝对相同的。我们这些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的看法就是始终如一的吗?也不是!再伟大的人物的思想也不是所有人在所有人生阶段都能够接受的思想。伟大人物的思想的唯一标志是一旦接受了它就再也无法完全回到此前的原初状态,再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的影响,然而也不是人人都把它奉为神明。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所有对鲁迅的不满乃至反叛都还没有真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都还停留在一种直观、直感的层次上,而这也就是它的过渡性、不稳定性的表现,并且虽然他们表现的都是对鲁迅的不满,但他们的不满又往往是彼此矛盾的。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大超过了他们彼此与鲁迅之间的矛盾,有的人甚至用鲁迅的主张、鲁迅的语言攻击鲁迅。这些不满不是没有任何道理,但这些道理都是在一种过程中随时可以变化的,正像人的直观感受是经常变化的一样。今年的流行色是蓝色,明年的流行色就可能是红色了。只有那些有了理性框架支持的感受,才能在较长时间中保持不变。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只有层垒式发展而没有急剧转折式变化的研究领域几乎只有鲁迅研究界,其他所有社会文化领域几乎都像折跟头一样翻了几翻。这说明这些文化领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理系统,没有一个牢固的统一的基础。它们是在变化中形成这种基础的,而在没有这个基础之前,它们也不可能确定与鲁迅的关系,他们的鲁迅观还会有急剧的变化。以下是我所说的对鲁迅不满的四方面表现。

外国文化研究领域
新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部分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介绍、输入、借鉴外国文化的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倾向。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开放过程中走入中国文化界的,他积极介绍和输入外国文化,这原本不会影响到鲁迅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但由于鲁迅当时的世界文化思潮与现在的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所输入的具体文化学说与鲁迅当时所重视的文化学说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上是矛盾对立的。他们重视的是当前的西方文化思潮,在他们的心目中,鲁迅就有些过时了,因此,他们对鲁迅的文化思想也持有一种否定态度。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开放又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的,它是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西方那些旧的和新的学说在中国都呈现着极为新鲜的色彩,对它们的直接运用一时也很有效用,但西方任何一种现成的学说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这在开始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西方文化学说以很快的速度轮流执政,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普遍的重视乃至信奉。现实主义很快变为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很快变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很快变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很快变为解构主义,在每一个小的发展阶段上,人们都是以当时最走红的具体思想文化学说为标准感受鲁迅、观照鲁迅的,鲁迅自然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但一旦把由于半个世纪的封闭所隔膜了的西方文化学说都陆续介绍到中国,一旦这些学说本身变得并不稀罕,我们就会看到,外国文化输入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学说,而在于我们自己思维方式的变化,在于我们能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一旦进入这样一种思考,鲁迅当时输入和介绍的具体学说的局限性就会变得并不像现在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认为的那么重要,而鲁迅在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之后对中国文化的解剖和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才是更为重要的价值,在这方面,并不是每一个外国文化的研究者都能做得如鲁迅那么好。当然,在这方面还可能出现新的甚至比鲁迅更伟大的中国文化巨人,但即使这样的文化巨人,也不会轻视鲁迅;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是比我们更为重视鲁迅的人,正像爱因斯坦比我们更尊重伽利略、牛顿,马克思比我们更尊重康德、黑格尔一样。我们对他们的观照是从外面进行的平面比较,我们要在对他们的比较中选出一个更伟大的来供我们宣传和介绍,供我们信奉,并作为我们衡量其他事物的标准。他们重视的是创造性行为的本身,在这种创造性行为上,前人未必渺小,后人也未必伟大。但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是比伽利略和牛顿都伟大的,马克思是比康德、黑格尔都伟大的,但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自己怎么看呢?恐怕和我们是不同的。外国文学界对鲁迅翻译中某些错误的指正,对他的翻译思想的质疑,都是合理的,但一个真正杰出的外国文化学者,是不会把这些问题当作多么了不起的问题的。他们知道何为大者,何为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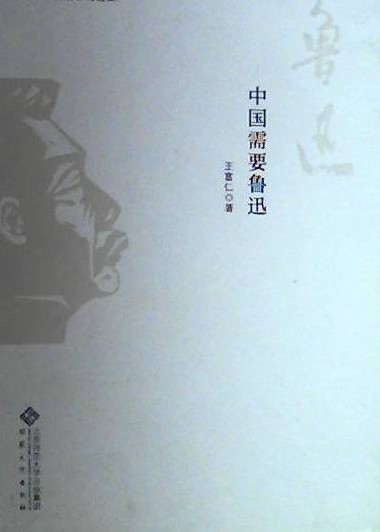
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几乎所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有些现代作家还是用鲁迅的话予以否定的。当新时期重新恢复这些作家的文学地位时,常常也伴随着对鲁迅一些言论的质疑或否定。这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中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对鲁迅的一些言论起到了一定的矫正作用;但从整体看,却表现为一种对鲁迅的否定趋势,这也使鲁迅在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心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但是,必须看到,鲁迅及其作用原本就不是在他独霸文坛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而是在与这些作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我们,包括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往往认为,对鲁迅之外的其他作家否定得越多、越彻底,就越能显示出鲁迅的伟大,而一旦别的作家也获得了很高的文学地位,鲁迅就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伟大了。这是中国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排座次的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任何人的伟大都是在一个背景上的伟大,这个背景越大,只要这个作家还没有在这个背景上消失,这个作家也就越伟大。文学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也是一样。文学崇尚的是多样化,如果我们天天看的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不论这部文学作品多么伟大,我们都会看烦了,都会转而厌恶它、轻视它。不能不说,现在一些人对鲁迅的厌恶,正是我们硬按着他们的头让他们读鲁迅作品的结果。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再好,你也不能天天看;贝多芬的音乐再好,你也不能天天听。天天看,天天听,它们就不好了。正是在众多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你才能感受到哪些作品在你的感受中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哪些作品是值得反复回味的,亦即哪些作品是真正伟大的作品。与此同时,伟大可以掩盖渺小,但绝不会掩盖伟大。普希金没有掩盖住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没有掩盖住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掩盖住卡夫卡,在所有现代作家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之后,鲁迅的价值绝不会比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表现得更微弱,而是将更加充分。现在,这个翻案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观念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即从个别比较的方式转化为整体观照的方式。在这个整体观照中,鲁迅的光焰消失了吗?没有!他的亮度更大了。他没有被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穆时英、穆旦、张爱玲、钱锺书的光焰所掩盖,他的独立性、独创性的思想和艺术的才能表现得更充分了。所以,此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鲁迅的否定倾向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它的影响尽管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但它不会构成多么强大的思想潮流,我们不必把它看得过重过大。和外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情况一样,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这些言论也不可能构成真正的联合阵线,它们联合不起来。研究高长虹的同研究徐志摩的不是一回事,研究梁实秋的同研究夏衍的不是一回事,研究胡适的同研究陈寅恪的也不是一回事,他们对鲁迅的不满都是一些矛盾着的不满,他们自己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倒带有更加绝对的性质。只要我们从分别的考察返回到整体格局的考察,我们就会感到,倒是从鲁迅及其文学观念、思想观念的角度,更能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他批评过高长虹,但没有否定高长虹;他批评过林语堂,但没有否定林语堂;他批评过胡适,但没有否定胡适。他与他们有差异、有矛盾,甚至有时是很尖锐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法国足球队和意大利足球队、英国足球队、德国足球队那样的矛盾,不是刘邦和项羽或岳飞和秦桧那样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复苏和繁荣也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对鲁迅的不满。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他是反传统的。在中国文化研究重新开展的过程中,鲁迅受到一些否定也是必然的。特别是新儒家学派,更是表现出明显的“反鲁”倾向。但是,新儒家学派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学派,而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学派。他们是在现代中国思考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问题的,而不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上思考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的,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学派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现代中国的伦理道德建设确确实实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他们企图通过对中国固有伦理道德的重视来克服现当代中国道德紊乱的状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更不乏合理的成分。但这毫不意味着应当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反映着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要求。中国社会的结构形式变化了,固有的伦理道德已经无法起到维系中国社会的作用,这种观念应该变化,也必须变化。在新儒家学派的势头正盛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也感到它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似乎新儒学对五四新文化否定的势力是不可阻挡的,也随之否定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局限性来。我在当时的课堂上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即使中国的男性公民全部成了新儒家学派的拥护者,至少还有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女性会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被彻底否定的,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已经不仅仅是男人的社会,仅此一条,新儒家就不可能像旧儒家那样统治整个中国。我认为,新儒家学派的唯一希望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鲁迅,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当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的问题。伦理道德不仅仅是理论性的,同时还是实践性的。孔子的伦理道德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是因为孔子及其后继者中确确实实有很多人不但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中贯彻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原则,不论他们历史作用的好坏,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的人物。这到了中国现当代社会中,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体现中国现当代人的道德情操的已经不是新儒家学派的提倡者,而是像鲁迅、李大钊、胡适这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儒家学派的领袖人物仍然恪守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但人们对他们的观点却有了变化。人们仍然不厌恶他们,甚至尊重他们,但却不会认为他们是最高社会道德情操的体现者。我是从《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建立起对鲁迅道德人格的尊重的,新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缺少的恰恰是这种反专制压迫的正气和勇气。总之,新儒家学派重视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的意图是十分可贵的,但通过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反对鲁迅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他们的贡献是在学术上的,不是在中国现当代伦理道德建设上的,他们对鲁迅的否定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真正对鲁迅精神有严重消解作用的是道家文化精神。在中国,对“为人生的文学”的否定,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及其鲁迅文化选择的否定,本质上都是从中国道家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它与康德等西方美学家的美学观之间的根本差别是:康德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而中国这些知识分子则是在否定启蒙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现当代道家文化的提倡者与中国古代道家文化的创立者之间的不同是:中国现当代的道家文化的提倡者仍然是一些社会知识分子,他们是在现代社会内部的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而不是在社会关系之外生活的。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社会要求,不是没有现实的社会关怀,而是感到无力实现这种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不真正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真正反对鲁迅。他们人数众多,恐怕连我们这些鲁迅研究者中实际奉行道家文化传统的也不在少数。别人我不知道,至少我自己是如此。我们在青年时期热情过、追求过,但现在我们成了教授,成了研究员,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虽无高官厚禄,但也满足,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我们仍然是关怀的,但总觉得那是一些与己无关的社会问题,有些空洞,有些不着边际,对于自己更为重要、更为切近的是个人平静生活的维持。我们缺乏鲁迅那种把社会和个人糅为一体、把社会追求同精神自由熔为一炉的感觉。这也难怪,先儒后道、外儒内道从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传统。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关心社会不如不关心社会,只要有了一个稳固的瞰饭的位置,少管一些“闲事”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中国有众多人口,但真正关心着我们民族的整体发展并以此为基础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文化道路的人恐怕并没有几个。这才是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最最核心的问题,也是鲁迅之所以宝贵的地方。但我们这些人却不会从根本上反对鲁迅,因为我们到底不是主要生活在大自然中,而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在实际的文化选择上不会像鲁迅那么“傻”,却能知道鲁迅的价值,不否定鲁迅的价值。否定鲁迅价值的是那些享乐主义者。当我们这些所谓“上层”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社会关怀,当我们自己实际重视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物质生活,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社会成员就把自己的追求目标转移到物质利益上去了。在这时,个人的、感官的、本能的、直觉的、物质的、实利的、性的就成了唯一重要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体,成了一种价值、一种美。鲁迅虽然并不否定人的本能的需求,但他的存在价值到底是社会性的、精神性的,在物质享乐方面,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他体现的也是偏于落后的倾向。我认为,这个阶层对鲁迅的否定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鲁迅不会跳舞,不善交际,在性关系上偏于拘谨,重美术而轻音乐,习于书斋,懒于出游,精神活动多于体育活动,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甚至就不活泼,等等,这些都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有着较大的距离。但是,享乐主义在整个社会上只是极少数人能够实际地得到贯彻的,在历史上只在短暂的历史阶段能够成为主要的思潮,在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只是有限时间内的实际思想倾向,它的纯个人性使其无法获得社会性的价值,即使一个享乐主义者也不会真正尊敬另一个享乐主义者,应伯爵也骂西门庆,潘金莲也忌恨李瓶儿,它的直感性使其无法获得精神性的价值。人不能没有感官享乐,但也不能仅有感官享乐。仅有感官的享乐,精神上就感到空虚了。所以享乐主义对鲁迅的否定是彻底的,但其过渡性更为明显。从个人而言,当享乐主义者感到一种精神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将更重视严肃的思想、沉重的感觉,他们原来认为是鲁迅缺点的东西,虽然仍然是缺点,但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精神生活上的丰富性、充实性;从整个社会而言,享乐主义使社会迅速分化,阶级阶层间的差别迅速扩大,人与人的感情关系变得极不可靠,甚至相互嫉妒、仇视,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动荡加强。对于更多的人,想享乐也享乐不起来了,对于他们,社会的关怀不再仅仅是对别人的关怀,同时更是对个人的关怀。鲁迅的价值在这时候又会成为人们不能不重视的东西。总之,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上仍然是最有实际影响力的,它不能不时时产生对鲁迅的否定倾向;但中国社会的结构到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每一次复兴,都孕育着自己新的否定力量的出现,鲁迅著作在中国文化由旧蜕新的过程中仍将持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领域
我说我现在属于胡适开创的中国学院派文化传统,那么,中国哪一部分知识分子才真正属于鲁迅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呢?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但恰恰是在这个领域,对鲁迅的调侃是最火热的,这可以称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大奇观。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在学院派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化趋势中产生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不论是文学创作界的作家、诗人,还是学院派的教授、学者,都希望开放,希望自由。大家彼此都有点同情、有点理解,彼此之间也能相互扶助。刘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作家出来叫好,评论家出来评说,鲁迅的有关论述也成了为刘心武辩护的理论根据。虽然彼此也都知道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却没有觉出彼此有什么不可忍受的地方。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自都有了更多一些的发展空间,自己可以顾上自己了,彼此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并且这种差异成了我们可以互相歧视的理由。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是摆弄概念的,是讲方法论的,是重传统的,是从中外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或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那里获得自己的文学艺术观念的,而我们鲁迅研究者则是在鲁迅作品的基础上获得这种观念的,在获取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把鲁迅概括化、抽象化了,同时又把文学的标准具体化了。我们眼中的鲁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家,是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的,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是后来走上了革命文化道路的,是一个“左翼”作家,等等。这些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但这是鲁迅自己,而鲁迅却不是只承认自己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而不承认别人也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的;不是只承认自己的作品是文学作品而别人的作品就不是文学作品的。也就是说,鲁迅是一回事,鲁迅的实际历史作用又是另一回事;他自己做了什么是一回事,他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和价值是怎样的又是另一回事。他开垦了新文学这块处女地,然后在这块处女地上种上了第一季的庄稼,他种的是豆子和玉米,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代人也必须种豆子和玉米。他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他是这块处女地的开垦者和保护者。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守护神,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守护神。他的所有的战斗都集中在反对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的斗争中,集中在让中国社会能够接受和理解新文化和新文学上。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特别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但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却常常是按照鲁迅实际表现出来的样子形成我们的文学艺术观念的,我们也用这样的文学艺术观念看待当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也用这样的标准要求他们、衡量他们。我们是在传统中形成我们的观念的,而一个创作家依靠的却不是我们的传统。他们也读过鲁迅的部分或全部的作品,但却不仅仅读过鲁迅,他们依靠的不仅仅是鲁迅的传统,他们读过的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他们的传统。并且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文学传统进行创作的,更是依靠他们实际的人生、实际的人生体验或当前读者的需要进行创作的。“传统”这个词是我们学院派知识分子搞出来的,对于创作家的创作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他们像孙悟空一样是从当代生活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个生活创造了他们,他们则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的作品。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们的作品一定像谁的和不像谁的,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他们想说什么、为什么说、怎样说。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是批评他们不像别人,而是批评他们不像自己。但我们却常常不是这样,而是要求他们说出我们能够满意的话来,并且得按我们喜欢的方式说。我们只愿意理解名人、要人,却不愿意理解他们。我们和当代作家在情感上就有了距离。一旦情感上有了距离,这个仗就打热闹了。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人家看不起我们的传统,看不起我们这些又穷又酸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就杀到我们鲁迅研究界来了,就来抄我们的老窝来了,就骂起“我们”的鲁迅来了。但他们把鲁迅当“我们”的来骂,实际上鲁迅并不是“我们”的,而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如果真的分起你我来,鲁迅倒是“他们”这些创作家的,而不是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不是我们更像鲁迅,而是他们自己更像鲁迅。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向来是温文尔雅的,他们嘲笑的所有鲁迅的那些“劣迹”,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是很少有的,倒是他们自己很难避免。因为他们都是创作家,都是在实际的生活之流当中的,都是根据现实需要进行选择的,都是很难做到完美无缺的。即使是同一部作品,也是要说好就能说好,要说坏也可以说坏的。实际上,鲁迅是不能像他们这样说的。鲁迅是个作家,对作家及其作品需要的是研究,不是像对平常人那样只做人品挑剔,也不是像生活检查会那样进行缺点和错误的批评。要谈鲁迅,就得下点工夫亲自去了解鲁迅,不能只听别人说他好或说他坏;并且要多读一些鲁迅的作品,不能根据对一两篇作品的直感印象就对整个鲁迅下结论;甚至还得对鲁迅研究有点起码的了解,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喜欢鲁迅,为什么有人又不喜欢鲁迅。只有把这些都了解清楚了,自己应当怎样看待鲁迅才有一点扎实的根据,才不致说的尽是些言不由衷的话,才不致流于主观武断,让人觉得有点霸道,有点目中无人。鲁迅不是圣人,我们也不是圣人;别人不能根据鲁迅的只言片语就轻易给鲁迅下一个结论,我们也没有资格仅仅根据自己的一点直感印象就给鲁迅下一个什么样的结论。现在某些当代作家对鲁迅的讥评之所以仍然停留在述说直感印象的阶段,就是因为他们对鲁迅的讥评并不是真的建立在对鲁迅的直接了解上,而是通过讥评鲁迅发泄对我们当代和当代鲁迅研究者的不满。而这种发泄方式本身就是不具有确定性的,就是极易发生变化的。到人们不用鲁迅压他们了,他们的发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了。鲁迅早已死了,他们在创作上的成功与失败,在人生道路上的顺利与挫折,实际是与鲁迅没有什么关系的。到他们真正冷静下来,不是把鲁迅当作必须逾越的障碍,而是把鲁迅也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一个人和一个作家,他们就没有这些怨气了;即使有怨气,也不会往鲁迅身上撒了。
总之,新时期以来确确实实有好多对鲁迅不满的言论,甚至有的言论充满了明显的敌意,但我认为,这都是一些过渡性的现象,不会构成统一的潮流,也不会有持续的影响,只是一些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的东西。就其整个发展趋势而言,我们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不是越来越萎缩,而是越来越发展。我们教育普及的程度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接受新文化、新文学影响的面在扩大,能够阅读和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人不是更朝着整齐划一化的生活发展,而是朝着多样化统一的社会发展。在这样一个社会上,必须依靠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思考,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在现代社会中求生存、求发展。鲁迅所体现的人生哲学倾向不是越来越为我们所不能理解,而是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中国人实际的人生观念和世界观念。至于鲁迅的世界影响,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外国人,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当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还没有认识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当这个人在自己的民族中还是一个受到普遍冷落的人的时候,世界是不会首先接受他、理解他的。我们老说鲁迅的世界影响还是很小的,但我们却没有说我们本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怎样看待鲁迅的。只要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成员不再把鲁迅当作自己的玩物,而是认真地研究他、阐释他,他在未来世界的影响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
总之,鲁迅是不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消失的,也是不会在世界上消失的。他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脆弱。因为他的思想不是脆弱的思想。
我对鲁迅充满信心,我对中国的鲁迅研究也充满信心!

作者:王富仁,1941年生于山东高唐。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2017年5月2日晚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名作欣赏:
0351-5256557
评论版:
0351-5256560
学术版:
0351-5256558
邮购:
0351-5256556
0351-5256557